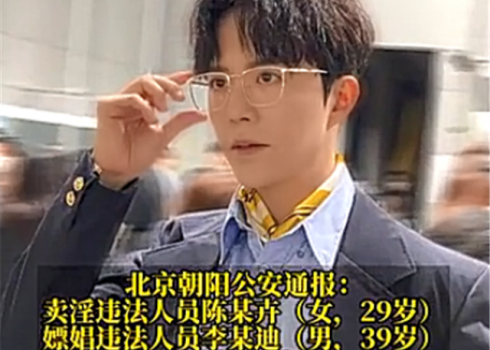广州南沙体育馆方舱一名新冠感染者自缢身亡,这是一则让人悲伤到不能自已的新闻。
这位化名小雅的广州女子,在11月18日上午自缢身亡,她离世的消息,在资讯便捷的互联网时代,经过了五天时间才传播开来。而在那篇刷屏的新闻报道中,我们大概能还原小雅活着时的一个生存剪影:
小雅,今年32岁,老家湖北天门,丈夫郑宇(化名),二人结婚十多年,有两个孩子,一个九岁一个五岁,留在老家,二人在外打拼多年,是典型的外来务工人员,从事服装制衣行业,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广州城中村,14日检出阳性转运方舱。
一个32岁的妈妈,抛下两个孩子不管,毅然决然地离开世界,她到底为什么而绝望呢?我们永远也无法走进她的内心,但关于小雅的死亡之谜,似乎仍然有一些蛛丝马迹。

在新闻中,我看到有这样一个细节,对于方舱生活,小雅并不习惯。而在得知丈夫也被感染以后,“她说过年也不想回老家了,留在广州,怕感染了这个病毒回老家被人说闲话”。
常年漂泊在外的小雅,难道不想回家团圆,不想见到孩子吗?她的害怕和恐惧,无非是担心阳性的标签,让她遭遇来自外界的歧视和非议,让她遭遇社会性死亡。
在她的自我定义里,感染新冠的自己,已经成了某种社会的“麻烦”,沾上了必须进行社交隔离的原罪。
报道说,小雅曾给她表姐打电话,“透露出对感染新冠病毒后的害怕,还在电话里哭了”。从这个细节来看,她似乎不只害怕感染后的社死,还害怕病毒本身,尽管她甚至没有出现发烧、咳嗽等症状。

至此,对于小雅的自杀,似乎可以有一个不太严谨的归因了。不管她在生前是否遭遇了其他的困难和挫折,新冠恐慌——对疾病本身以及对感染后社死的恐慌,无疑已成为了压垮骆驼的稻草。
如今,就像郑州官方说新冠肺炎是自限性疾病那样,对病毒的科普越来越多,但小雅之死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,在社会心理层面,新冠恐慌仍然是一种普遍性心态。
为什么?说到底,消除恐慌早已不仅是一个科普命题。
在一些用力过猛的措施下,在层层加码的尺度下,我们很难要求大家去理智地相信,新冠病毒不可怕。就算相信科普,感染后隔离封控以及社死的代价,同样会让大家畏惧恐慌。
可怕的不是病毒,而是巨大的不确定性。我相信,这种困顿的状态,不只是小雅一个人有。就像今天一篇刷屏文章提到的,新冠一代的孩子们,也正在亲历超出想象的“次生灾难”。

在与世界告别的时候,小雅的内心一定经历了剧烈的斗争和煎熬。新闻说,17日24时到18日8时,小雅整晚没睡,她用了8个小时来进行心理建设,最终还是没能找到一个说服自己继续活着的理由。
同样一片体育场馆,悲欢却并不相通。
我们为小雅之死而悲痛。她的离去,作为一种“排除他杀”的自杀行为,也许不会被纳入到五千多例新冠死亡病例的数据库中,但这并不意味着,可以轻描淡写的用自杀的定义这一场悲剧。
在某种意义上,小雅自杀,也代表了一种“次生灾难”。在其背后,长时间封控对收入、生存的影响,用力过猛造成的病毒恐慌心态,感染连带产生的社会性死亡,它所制造出的无法反馈到新冠统计数据层面的社会心理创伤,也在制造一起起悲剧,这一事实应该被重视、被看见了。
无论如何,我们始终不能忘却一点——所有的防疫措施,不是为了别的,正是为了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。
评论员熊志2022-11-24 01:34原标题 新冠恐慌下的广州方舱女子之死